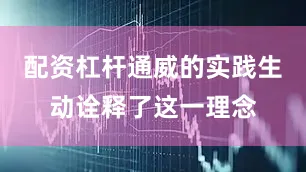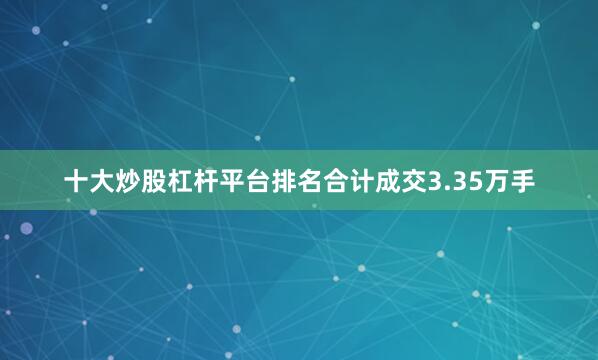引言:西进运动中的身份撕裂
《荒野猎人》(The Revenant, 2015)常被视为一部关于荒野求生的史诗,但若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切入,影片实则揭示了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中白人与原住民之间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,以及混血者格拉斯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身份困境。影片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,但导演伊纳里图通过视觉符号与叙事结构,将个人复仇故事升华为对殖民暴力、种族压迫与文化异化的深刻批判。
一、文明与野蛮的倒置:谁才是“野蛮人”?
影片通过三重对比解构了殖民话语中的“文明-野蛮”二元论:
1. 白人的野蛮性:
- 开场的剥皮场景中,猎人们将动物尸体堆积如山,而法国殖民者更悬赏印第安人头皮,将暴力商品化。
- 菲茨杰拉德(汤姆·哈迪饰)以“适者生存”为名抛弃格拉斯,却自诩为文明代表,其行为比原住民的“野蛮”更显冷酷。
展开剩余69%2. 原住民的抵抗逻辑:
- 雷族人袭击猎人营地的长镜头中,自然(树木、雾气)仿佛成为原住民的同盟,暗示其反抗的正当性。
- 吊死在树上的印第安人尸体旁挂着“野蛮人”木牌,讽刺白人将自身暴行投射为他者。
3. 格拉斯的矛盾身份:
- 作为白人与波尼族的混血者,格拉斯既被猎人群体排斥(菲茨杰拉德称其儿子为“杂种”),也无法完全融入原住民社会。
> 关键隐喻:黑熊袭击格拉斯时,镜头以第一视角呈现撕咬,象征殖民暴力最终反噬施暴者自身。
二、荒野作为殖民暴力的见证者
影片中的自然并非中立背景,而是殖民历史的沉默记录者与终极审判者:
- 水的双重象征:
- 开场的河流承载着皮毛与鲜血,指向殖民贸易的血腥本质。
- 结尾格拉斯将菲茨杰拉德推入流水,以自然之力代替个人复仇,暗合原住民的“自然正义”观。
- 马腹重生的隐喻:
格拉斯裸身钻入马腹的画面,既象征回归母体(自然作为哺育者),也暗示其文化身份的剥离与重生。
三、复仇的虚无与身份的和解
影片对传统复仇叙事进行了颠覆:
1. 复仇的徒劳性:
- 格拉斯放弃手刃仇敌,台词“复仇是造物者的工作”表明其意识到暴力无法终结殖民创伤。
2. 身份的和解可能:
- 结尾雷族人无视格拉斯离去,暗示原住民对“中间者”的漠然接纳;而格拉斯凝视镜头的眼神,传递出对归属的永恒迷茫。
> 导演意图:伊纳里图曾表示,影片试图展现“暴力如何摧毁一切,包括施暴者”。这一主题通过格拉斯的身体创伤(失语、疤痕)与精神异化(幻象、兽性)具象化。
结语:未完成的赎罪
《荒野猎人》的深刻性在于,它并未给出殖民伤口的愈合方案,而是通过格拉斯的旅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:在殖民逻辑下,无论是征服者、被征服者还是混血者,最终都成为暴力的囚徒。影片结尾的开放式构图,恰如美洲大陆未完成的种族和解——雪原茫茫,出路何在?
发布于:江苏省通弘网配资-配资炒股-股票开户-股票市场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公司官网
- 下一篇:没有了